
走廊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
作者简介:李大龙,河北沧州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融史研究”(项目编号:17ZDA176)。

摘要
在综合分析国内学界走廊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不同学科对走廊的界定不同,研究目的各异,费孝通先生倡导走廊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诠释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进而对民族学界提及的六大走廊做了具体分析,并提出可以用“榫卯”来重新阐述这些走廊在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走廊;中国疆域;中华民族;榫卯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走廊”一词本来是建筑学上的术语,被引入社会研究却成为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但主要集中在民族学、人类学以及经济学和国际关系领域,最近两年也得到了边疆学研究领域学者的关注。实际上就历史学而言,“走廊”的研究也很早就得到了重视,且是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视域下给予关注的,谷苞先生发表在《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上的《论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意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该文后来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了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中。[1](P276-291)遗憾的是这种研究视角并没有为学界继承和持续下来。从研究的目的而言,民族学/人类学与历史学虽然都是从人类社会的视角关注“走廊”,且给予走廊以高度关注,但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别。因此,笔者试图在分析学界“走廊”研究的基础上,对民族学/人类学和历史学关注的“走廊”之间的差异,及其在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中的贡献做初步探讨,以供学界同仁参考,共同推进走廊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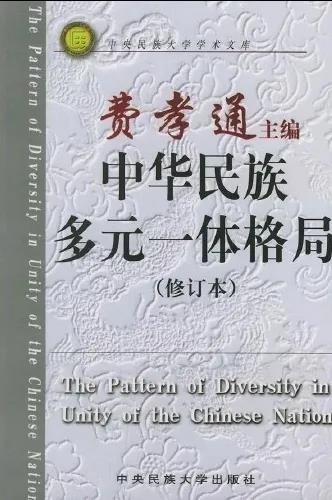
国内学界对走廊的研究从研究对象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对中国疆域内部河西走廊、藏彝走廊、辽西走廊、苗疆走廊、岭南走廊、武陵走廊等走廊的研究;二是对中国联结世界的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一中亚一西亚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一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六大经济走廊的研究。对于前者的研究,应该说国内学界已经有了长期的积累,而对后者的研究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出现增长的态势,并且为前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由此也可以说走廊的研究当前呈现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
通过中国知网可以检索到题名中含有“走廊”的中文文献是8 130篇,年度分布是1998年只有118篇,2004年增长到217篇,2014年是477篇,2019年达到了572篇。其中主题涉及河西走廊(包括甘肃走廊)的是2450篇,占30.1% ;经济走廊(包括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的是1 146篇,占14.1%;藏彝走廊(包括民族走廊)的是346篇,占4.3%。如果按照学科分类,属于经济(包括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方面的文献是1 949篇,占23.97%;环境方面的文献是258篇,占3.17%;民族方面的文献是247篇,占3.04%;历史方面的文献225篇,占2.77%。这些文献涉及的关键词有:河西走廊(包括河西走廊东部、河西走廊地区)1 167篇,占14.35%;中巴经济走廊149篇,占1.83%;中蒙俄经济走廊146篇,占1.8%;藏彝走廊(包括藏羌彝走廊)169篇,占2.08%;南岭走廊38篇,占0.47%%;辽西走廊35篇,占0.43%;苗疆走廊35篇,占0.43%;武陵民族走廊24篇,占0.3%。①
综合分析上述检索数据不难看出,国内学界对走廊的研究有以下值得注意的特点:
其一,从论文数量上看,走廊研究在世纪之交开始得到学界关注,而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渐成研究热点,且呈现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及国际关系诸多学科学者共同参与的态势。
其二,学界对走廊的研究无论是从涉及的主题、学科分类还是关键词,依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国内河西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河西走廊、苗疆走廊及武陵民族走廊等的研究;二是对中巴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国际经济走廊的研究,两者的研究目的除河西走廊研究存在交叉外,也有着明显不同。
其三,对走廊的研究尽管涉及诸多具体的走廊,但主要是集中在经济领域,即便是对河西走廊的研究也基本上多是在丝绸之路的视角下进行的研究,从民族或历史方面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仅仅占到了论文总量的5.81%。
由此可见,走廊作为近年来被学界屡屡论及的研究对象,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界定和具体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也有明显不同。就经济研究领域的走廊而言,国际性的经济通道一般被视为走廊,既可以是交通线网,如新欧亚大陆桥,也可以是区域性的,如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应该说,将走廊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从经济发展的视角进行研究,视野更为宏大,也为传统的走廊研究,如河西走廊研究等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多数学者对走廊研究的视角和目的也脱离了以往的关注国内的传统,而且有些研究只是借用了“走廊”的概念,诸如六大国际经济走廊的研究,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统走廊研究。基于此,本文还是试图将研究视角限定在民族学研究所谓“六大民族走廊”上,从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视角,对走廊的作用做系统阐述,以求正于学界有志同仁。
二、走廊的分类:两种不同性质的走廊

尽管很早就有河西走廊、辽西走廊等有关走廊的用法,但在民族学领域,费孝通先生是较早提出“走廊”概念的学者之一,在《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一文中又明确提及了藏彝走廊、河西走廊与南岭走廊三个概念:“那个地带就是我所说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我也曾称它作藏彝走廊,包括从甘肃,到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洛瑜地区。”[2]“广西、湖南、广东这几个省区能不能把南岭山脉这一条走廊上的苗、瑶、舍、壮、侗、水、布依等民族,即苗瑶语族和壮傣语族这两大集团的关系都搞出来。”[2]“西北地区还有一条走廊,从甘肃沿“丝绸之路’到新疆。在这条走廊里,分布着土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等,他们是夹在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中间。”[2]费先生是将关于走廊的研究纳人对民族、民族关系乃至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阐释中。此后,关于走廊的研究成为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尽管在对走廊数量的认定方面学者还存在不同的认识,但对河西走廊、藏彝走廊、辽西走廊、苗疆走廊、南岭走廊、武陵走廊六大走廊的看法似乎已经是民族学界的一般认识。
河西走廊,或称为甘肃走廊,是位于黄河以西,夹在祁连山和合黎山、龙首山等山脉之间,东起乌鞘岭,西迄甘肃与新疆交界,东西长约一千公里,呈西北一东南走向的狭长地带,因为形如走廊且地处黄河之西,故被人们称之为“河西走廊”。
藏彝走廊,如上所述是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李绍明认为:“大多数人认为藏彝走廊与横断山脉、横断山脉中的六江流域关系密切。实际上,横断山脉中的六江流域是藏彝走廊的主要区域,与藏彝走廊大部分地区重合,但横断山脉也不是全部在藏彝走廊内。”[3]结合上引费孝通先生的认识,可以说尽管存在藏彝走廊的概念,但其具体所指,学界尚未有一个确切的认识,只是有一个大致的范围认定。
辽西走廊,似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指位于燕山山脉与渤海之间的区域,这一区域存在着沟通东北地区与中原的交通网络,辽西走廊之称概由此生。广义则应该包括辽河以西地区。崔向东认为“辽西区域即指燕山山地以北,西拉木伦河以南,医无闾山以西和七老图山以东的区域,但其核心区域主要在今辽宁西部朝阳、锦州、葫芦岛和阜新等地。”“所谓‘辽西走廊’,指的是分布于辽西地区的连接中原和东北两大地域的交通廊道。辽西为丘陵地带,古道多沿河谷而行,河谷两侧山脉夹峙,中间一线之路蜿蜒透迄,实为名副其实的交通廊道。”[4]
苗疆走廊又称“古苗疆走廊”,是杨志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苗疆走廊是指:“从地域空间上看,主要指的是明代以后正式开辟的起于湖广常德,经辰州(沅陵)、沅州(芷江)等地,东西横贯贵州中线的所谓人滇‘东路’或‘一线路’,沿这条古驿道形成了一条穿越数省、长达千余公里,涉及数万平方公里面积的狭长地带。”[5]此后关于苗疆走廊的研究逐渐得到学界尤其是贵州民族学界的关注。
南岭走廊又称“南岭民族走廊”,如前所述是费先生提出的概念,是指分布于江西、湖南、广东和广西的南岭山脉地区。南岭又称“五岭”,是由一系列不连续的山地组成,麻国庆认为南岭走廊“应包括武夷山区南端、赣南山区、粤北山区、湘南山区、桂东北山区、桂北一黔南喀斯特区、滇东高原山区,东连闽粤沿海,西接横断山脉(‘藏彝走廊’区域)及东南亚山区。”[6]
武陵走廊,有学者称为巫山一武陵山走廊,也是费先生首先提出。李星星认为其范围是“东北一西南走向的巫山、武陵山、雪峰山及清江、沅江流域地区”。[7]
对于上述六条走廊,尽管学界都以“走廊"称之,但实际上按照“走廊”一词的原意来说只有河西走廊、辽西走廊、苗疆走廊具有明显的交通通道的性质,符合其标准,而藏彝走廊、南岭走廊、武陵走廊等虽然用了“走廊”二字,不过由于处于山脉的自然环境之中,其交通通道的特性并不是十分明显。也就是说,目前国内民族学界关注的这六条走廊也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第一,具有明显交通通道特征的走廊,河西走廊、辽西走廊和苗疆走廊即是。第二,交通通道特征不明显但却是属于费先生所说“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藏彝走廊、南岭走廊、武陵走廊即是。至于费孝通先生为何将不同性质的区域通称为“走廊”,未见其有明确的阐述,由此也引发了学界的一些争论,尤其是在如何对走廊做出明确界定方面。
李绍明是积极响应并推动走廊研究的学者,在认定“走廊原本是建筑学的一个概念,指一种建筑形式”的前提下,经过反复之后,将走廊定名为“民族走廊”,并给出了如下定义:“民族走廊作为一个民族学概念有其特殊的含义,它必须以地理学概念的走廊运行为前提。简言之民族走廊的特殊含义在于,某- -或某民族长期移动的路线必须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的走廊环境中,始可称之为民族走廊。”[8]李先生的界定在民族学界影响很大,但遭到了李星星的质疑,并对“民族走廊”做了重新定义:“‘民族走廊’是在中国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处于古代冲积平原农业文明区域边缘、属一定历史民族或族群选择的、多半能够避开文明中心政治经略与开发、既便于迁徙流动又便于躲避以求自我保存的其地形复杂而又依山川自然走向平而呈条带状的特殊地带。这些特殊地带也是中国少数民族的摇篮。”[9]实际上,恰如李星星上文中所言,费孝通先生并未明确提出“民族走廊”的概念,但“民族走廊”的提法似乎也并未正确理解费孝通先生的意图,而李星星在此基础上试图用“二纵三横”格局来概说中华大地上的“民族走廊”更是误读了费先生提出“走廊”概念的目的。
如前引费先生所述,提出“南岭走廊”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一条走廊上的苗、瑶、舍、壮、侗、水、布依等民族,即苗瑶语族和壮傣语族这两大集团的关系都搞出来”。也就是说,“走廊”是被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带”提出的,无论是河西走廊,还是南岭走廊、藏彝走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一个狭长的多民族分布的“地带”,注重对这一“地带”中各民族之间关系的研究是提出“走廊”概念的目的,而非“走廊”研究本身。因为只有这样的探讨,才会体现出一个区域内民族和文化的“多元”关系,进而才能更好地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提出做重要的铺垫。关于这一点,在费孝通给“‘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的贺信中已经有很明显的体现:“六江流域天然的河谷通道,民族种类繁多,支系复杂,相互间密切接触和交融。对这条走廊展开文献和实地田野考察,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学家能看到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和这一历史的结晶,从而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比较生动的认识。”[10](P1)"六江流域天然的河谷通道”和河西走廊所具有的交通通道性质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二者所具有的多民族分布却是共同的特点。前者“民族种类繁多,支系复杂”,后者“这条走廊里,分布着土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等等”,探讨多民族如何共存于同一个“走廊”之中,如何共同发展,自然可以很好地诠释“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进而也可以得出“一个比较生动的认识”。
由此看,尽管存在两种不同的走廊形态,但费孝通先生提出走廊研究的目的并不仅仅限于研究“走廊”本身,而之所以提出和积极推动走廊的研究,既是费孝通先生为构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做的前期准备,同时这种探讨也有助于人们更准确的理解“多元一体格局”这一理论。基于此,笔者虽然认为“从‘多元’走向‘一体’的理论不仅可以被视为解读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有效途径,对于解读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乃至区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等等,都具有理论范式的重要作用”,[11](P3~11)从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背景下审视两种“走廊”在其中的作用,对于我们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疆域和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等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和意义。

三、榫卯:走廊与不同区域、族群和文化的凝聚与交融
众所周知,“走廊”一词源自建筑术语,既然费孝通先生可以用其来诠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那么笔者也想用同样源自建筑的词汇“榫卯”来诠释两种走廊在中国疆域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榫卯结构是古代中国建筑的主要构成方式,即通过两个构件凹凸部位的相连接,不用钉子和胶的粘合即可以实现建筑的牢固,这体现着中国人超常的智慧,是中华文明优秀成果之一。如果将多民族国家中国的缔造视为是当今56个民族以及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众多民族共同的家园的话,这一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11](P2)呈现西高东低三级阶梯状。青藏高原是第一级阶梯,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等地形区构成了第二级阶梯,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东南丘陵等地形区则是第三级阶梯。是什么原因导致生息繁衍在不同自然环境下的众多族群成了这一家园的“家人”?共同的“家园”又是如何缔造的?这是中国边疆学和民族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建构迫切需要解答的基本问题。费孝通先生用“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来诠释“家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而史学界长期存在着用历代王朝的话语体系来阐述“家园"(中国疆域)的缔造过程。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则提出了用“自然凝聚,碰撞底定"来诠释“家园”和“家人”形成与发展的轨迹。[12]在这一视角下审视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族群共同缔造“家园”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是形如榫卯的两种走廊将不同自然环境的区域及其上生息繁衍的族群“榫卯”在了一起,为中国疆域和中华民族的“自然凝聚”提供了牢固基础。将青藏高原、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等“榫卯”在一起的是河西走廊,而真正使河西走廊发挥作用则是始于西汉武帝对河西的经营。西汉武帝之前,河西走廊先后是乌孙、月氏、羌和匈奴等控制的区域,在汉朝和匈奴对峙时期匈奴经常联合西羌威胁西汉的西部边郡。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在西汉的持续武力打击下,元狩二年(前121)管辖河西走廊地区的匈奴浑邪王率众降汉,西汉于河西走廊设置武威郡、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又分置张掖郡、敦煌郡。后世史书载:“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②上引谷苞先生文中重点阐述了河西走廊四郡设置对历代王朝经营西域的重要意义,但实际上不仅仅限于西域,河西四郡设置后成为西汉经略河西走廊以西西域,以北匈奴、以南西羌等地区的重要基地,而且更重要的是汉朝对河西走廊的经营为以后历朝各代所继承,丝绸之路的繁盛、盛唐文明的出现乃至近代国弱时领土被蚕食鲸吞状态下新疆建省能够成为中国疆域重要组成部分等等,这些历史事实皆是河西走廊的“榫卯”作用得到了完美发挥的表现。③
将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榫卯”在一起的是辽西走廊。尽管有学者认为辽西走廊的开发利用相对河西走廊要晚,“在辽金三百年的时间里,辽西走廊在交通、 军事上的重要地位逐渐形成”,[13]但其在上述三个地区族群交融与文化融通方面的作用却是早在史前就开始了。在辽西地区出现的红山文化因为代表性器物玉猪龙的出现而被视为中华文化的起源地之一。商末三贤之一的箕子东走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建立称臣于周朝的侯国朝鲜(箕子朝鲜),史称“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④西汉初期燕王卢绾反叛,“燕人卫满亡命,聚党千余人,椎髻、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淇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燕亡命者王之”。⑤这些史实说明辽西走廊已经在发挥着中原与东北乃至朝鲜半岛族群流动与文化传播通道的作用,而以好太王碑、璧画墓和山城为代表的高句丽文化,在盛唐文明影响下出现的“海东盛国”等都是这种族群流动和文化传播结出的硕果。辽金时期,辽朝的疆域东至渤海、东海(日本海)和北海(鄂霍次克海),西至阿尔泰山以西,南至白沟,北至外兴安岭,而金朝在辽疆域的基础上更是将南部疆域拓展到了淮河一线,[14](P874、1108)辽西走廊沟通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的作用更加凸显,这或许即是“重要地位逐渐形成”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明清时期,辽西走廊先是成为明朝经略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的主要补给通道,后是明朝和崛起的后金在傍海的辽西走廊地区展开了长达近30年的争夺战,其结果却是明朝失去了对东北平原的经营,而后金发展而来的清朝则在1644年越过辽西走廊入关,实现了对中华大地的“大一统”。史载:“顺治八年定,山海关外荒地甚多,有愿出关垦地者,令该管官造册报部,分地居住。”⑥“大一统”状态下的辽西走廊由此不仅成了华北平原移民⑦流入东北平原的重要通道,而辽西走廊的咽喉山海关也由军事防御的前沿兼有了移民中转站的功能,为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融为一体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北部地区不同,将东南丘陵地带、云贵高原与长江流域、四川盆地乃至青藏高原“榫卯”在一起的是南岭走廊、藏彝走廊和苗疆走廊。三条走廊在不同时期、不同方向发挥着同样性质的“榫卯”作用。
南岭走廊的重要作用在秦朝曾经有过一次完美体现。史载:始皇帝三十三年(前215),秦始皇“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略取南越陆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⑧秦朝的移民为秦汉之际南越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也为西汉武帝统一南越国,将郡县推广到南岭以南至今越南中部以北地区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史载:元鼎五年(前112)秋,汉武帝派遣“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群柯江;咸会番禺”。“吕嘉、建德以夜与其属数百人亡人海”,“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址、九真、日南九郡”。⑨秦汉对南部地区的有效经略让南岭走廊“榫卯”作用有了更为具体的完美体现。
苗疆走廊的形成尽管相对较晚,但其“榫卯”作用也十分明显。苗疆走廊是明王朝为了经略云贵地区而在元代驿站基础上开辟的重要通道。这一通道虽然从涵盖范围上看是联通今湖南、贵州和云南的元代驿路,但其“榫卯”作用从《贵州通志》的如下记载中即有准确体现:“贵州四面皆夷,中路一线,实滇南出入门户也。黔之设,专为滇设,无黔则无滇矣。”⑩贵州建省、军事卫所在苗疆走廊及黔滇的铺开乃至移民和文化的传播等,都是这一走廊带来的效果,称其为“维系内地与西南边陲往来的主要交通命脉,并且也直接影响了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地区政治版图的变化”,[5]是比较恰当的评价。
藏彝走廊的“榫卯”作用实际上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中已经记述的很清楚:“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諜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驢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西南夷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与共同性是藏彝走廊在族群流动和文化传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结果。石硕将藏彝走廊民族交往的特点归纳为两点:一是“主观上民族观念淡薄,民族界线模糊”;二是“文化普遍持包容态度,使各民族在文化上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5]应该说,正是这两个特点让藏彝走廊把四川盆地、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牢固的“榫卯”在了一起,共同成为“家园"(中国疆域)和“家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在六条走廊中,武陵走廊是最为特殊的一个,其虽然在地域上东联两湖,西接巴蜀,北邻关中,南为两广,地处华中腹地,但并不具备其他走廊的特点,是被称为“蛮”的族群的主要分布区域,现在则是土家族、苗族、侗族等的分布地区。武陵山脉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武陵地区族群强悍的民风,尽管反叛屡屡见诸于史书,但追求内地化的管理方式却是东汉以来的历代王朝努力的方向。《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永元十三年(101),巫蛮“以郡收税不均,怀怨恨,遂聚反叛”。永和元年(136),武陵太守上书顺帝称“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实施郡县化管理,并和当地汉人一样征收租赋,这种做法体现着汉王朝谋求对其实行与内地郡县同质化的管理方式。经过历代王朝的努力,“若就文化多样而言,武陵地区三大少数民族文化亦各有特色。土家、苗、侗均有自身独特文化,但此三族的文化又有相互交融的现象,且呈现出地域不同的变异”,[16]不过最终的结果却是同属于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走廊之所以能够起到“榫卯”的作用,特定的地理环境是先决条件,其内部族群与文化的交流与交融则是内在的基本条件,而来自走廊外部的政权的有效经营则是走廊能够发挥其“榫卯”作用的关键性条件,多民族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河西走廊的“榫卯”作用即有完美体现。这也是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诠释过程中历代王朝对“河西四郡”的经营成为其重要内容进行阐述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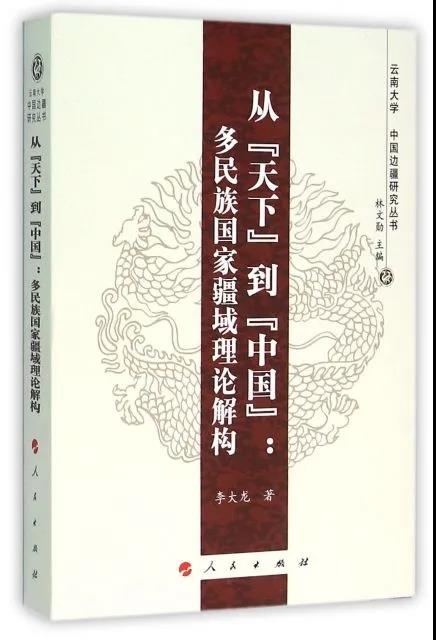
四、结语
走廊作为一个独特的区域,为不同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作为民族学研究对象的藏彝走廊、河西走廊、南岭走廊、辽西走廊、苗疆走廊和武陵走廊,学者们给予了充分关注,对于我们认识走廊内部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有着极大帮助,更有助于证明“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具有方法论范式的重要意义。但是,将研究视角仅仅局限于某一走廊,探究其内部众多族群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抑或是从走廊的视角来探究今天多民族中国范围内走廊的分布结构,以诠释似乎没有必要进一步论证的今日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多元”特点,似乎都难以充分体现“走廊”概念提出的巨大价值和意义。
毋庸置疑,费孝通先生提出“走廊”概念的初衷和目的是为了从“多元一体格局”视角诠释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回归这一研究初心,在诠释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探究上述诸多“走廊”的重要作用,不仅有助于推动国内学界的走廊研究,更有助于不同学科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尤其是边疆学有关多民族中国疆域话语体系的建设。将民族学领域提出的六大走廊在多民族中国疆域、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比喻为“榫卯”,能否准确而充分体现走廊的价值尚待学界同仁提出高见,这是笔者走廊研究的第一步。而主导或推动走廊发挥“榫卯”作用的因素除走廊外部历代王朝的经略外还有哪些,则是笔者以后重点研究的内容。与此同时,也期盼更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走廊研究,放宽视野,共同将走廊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注释
①依据中国知网的检索数据分析,访问时间:2020年2月3日。
②《后汉书》卷87《西羌传》。
③《中国民族报●理论周刊》从2017年5月26日至2019年2月1日先后刊发近20篇有关河西走廊的文章,其中2018年10月19日刊出的《河西笔谈:从河西走廊发现更广阔中国》,笔者是作者之一。针对“从“如何认识中国’定位河西走廊”,笔者明确提出了可以用“榫卯”定位河西走廊的巨大价值。参见黄达远主编:《从河西走廊看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④《后汉书》卷85《东夷●高句丽传》。
⑤《资治通鉴》卷20,元封二年正月条。
⑥《大清会典事例》卷1093《奉天府》。
⑦有关清朝东北移民政策的演变情况,参见范立君,谭玉秀:《清前中期东北移民政策评析》,《北方文物》,2013年第2期。
⑧《资治通鉴》卷7,始皇帝三十三年条。
⑨《汉书》卷95《两粤传》。
⑩(民国)《贵州通志》卷2,第521~522页。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2]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3).
[3]李绍明.藏彝走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4]崔向东.辽西走廊变迁与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4).
[5]杨志强,赵旭东,曹端波.重返“古苗疆走廊”一西南地区、民族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视阈[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2).
[6]麻国庆.南岭民族走廊的人类学定位及意义[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
[7]李星星.再论民族走廊:兼谈“巫山一武陵走廊”[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2). .[8]李绍明.再谈民族走廊[J].“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成都:四川大学,2003年11月.[9]李星星.论“民族走廊”及“二纵三横”的格局[J].中华文化论坛,2005(3).,
[10]费孝通.给“‘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的贺信[J].藏学学刊,2005年辑刊.
[11]李大龙.质疑、继承与发展——费孝通对中华民族理论阐述的重要贡献[J].中国边疆学,2018(1).[12]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3]吴凤霞.辽金时期的民族迁徙与辽西走廊滨海州县的发展[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14]林荣贵.中国古代疆域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
[15]石硕.藏彝走廊多民族交往的特点与启示[J].中华文化论坛,2018(10).
[16]李绍明.论武陵民族区与民族走廊研究[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